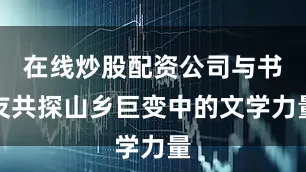
——访闽北作家上官晓梅
文/蓦烟如雪
上官晓梅,邵武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04年鲁迅文学院创作高级函授班学员。著有长篇小说《大唐婉儿》《山潮》,中短篇小说集《心锁》。作品散见于《作家文摘》《青年文学》《福建文学》《参花》等。《心锁》获福建省“首届海峡两岸文学创作网络大赛”三等奖,《大唐婉儿》获2022年“今古传奇”全国优秀小说一等奖,《山潮》获2023年“新时代福建山乡巨变”福建本土重点题材原创长篇小说签约作品扶持项目等。 多年来,上官晓梅笔耕不辍,且涉猎多种文体,如小说、散文、现代诗、近体诗、小品小戏等,近年又创作了一批新作品,如长篇小说《先锋》,短篇《伤兵》,小小说《电视机》《小保姆》《拾荒者》等。
6月27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闽北邵武作家上官晓梅携其长篇小说新作《山潮》做客福建省文学院,与书友共探山乡巨变中的文学力量。这本书以福建乡村为背景,书中有哪些别样的乡土情怀,带着疑问,本报记者对其进行独家专访。
展开剩余80%记者:看到你携新书长篇小说《山潮》做客福建省文学院,请问《山潮》讲述的是什么主题?
上官晓梅:《山潮》讲述的是一群山里人在改革开放中的故事。这本书的主题是歌颂党中央的“惠农政策”给乡村发展带来空前利好,如“道路硬化村村通”“农村医疗保险”等惠农政策都具有划时代意义。
记者:在分享会上,您谈及“创作灵感源于对故土蜕变的长期观察,试图以文字捕捉乡村振兴中个体生命的坚韧与希望。”作为闽北人,闽北给了您什么样的创作源泉?您认为应该用怎样的态度来写作?
上官晓梅:我是地道的闽北人,自然我的创作源泉来源于闽北这片故土,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带着闽北的气息。如长篇小说《山潮》的原点主要来源于我童年和少年时代居住过的村庄。
至于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写作,我的回答是“静下心来”。我之前几乎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就我自身来说好像不存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必要。这次作客福建省文学院分享《山潮》,有个专程从厦门赶来的姑娘,也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她说她很热爱文学,但为自己一直没有什么收获很焦虑,不知道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写作。我答道:你把写作当成种铁树,铁树可能十年一开花,也可能不开花,但是,铁树无论开不开花,它都是人们认可的独特的风景。你一旦拥有了这种心境和姿态,还怕铁树不开花吗?宋之问有两句诗可以很好地诠释:“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
记者:说到乡土,我们会想到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乡土中国”,以及“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等经典论断。在活动现场,您提到“真诚是连接作者与土地的纽带”,能否展开谈谈您对这句话的深入理解?
上官晓梅:可以的。我所说的“真诚”,首先是人类对土地应有的敬畏与感恩。我曾在诗中写道:“稻穗弯下腰,是对土地的敬畏,每一粒谷种都连着泥土的血管……一次次为人类呼唤黎明的不是太阳,而是黑土地。”土地不仅是滋养万物的根基,更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是传承文化和情感的根基。所以,作为一个创作者,唯有怀着赤诚之心扎根土地,才能真正触摸到乡土文化的内核,捕捉到大地脉搏的跳动。这种真诚,既是对土地馈赠的珍视,也是用文字反哺土地的责任,只有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土地的呼吸融为一体,笔下的文字才能生长出打动人心的力量,让乡土的故事与精神代代相传。
记者:小说《山潮》围绕着山乡时代巨变,书中有许多鲜活的小人物,如最先“吃螃蟹”的人,再如发誓无论多难都要修一条路,努力提升村庄质量的村长李海龙,抑或是为弱势群体垫付医疗费的小人物等等,在这些故事里,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个小人物?
上官晓梅:印象最深的当然是主人公李海龙和王僖月。李海龙当选村长后,历尽艰难,为村里修了一条长达十几里的马路,通往山外,而他自己却因过度劳累耽误病情最终离开了人世。另一个王僖月,她在城里打拼,发达做大做强起来后,能够做到喝水不忘挖井人,回馈家乡,投资搞家乡建设。这种思想境界,把整个乡村巨变从物质升华到精神层面的巨变。
记者:看到您写过各种体裁的作品,如小说、散文、诗歌、近体诗,小品小戏等,不同题材的作品写作手法技巧跨越很大,您是如何精准把握不同题材的创作思路和技巧的。
上官晓梅:在我看来,所有文学体裁都是表达的容器,而故事、情感与思想才是永恒的内核。无论是千余字的微型小说,还是鸿篇巨制的长篇,本质上都是对人性、对世界的不同切面的观察与拷问;就像画家既能画磅礴山水,也能勾勒精微小品,技法或许有别,但艺术是相通的。所以,多题材的写作,反而能让不同体裁之间碰撞出火花,从中获得启发,如诗歌的张力可以融入散文,微小说的跳跃结构可以增添散文留白等等。
记者:您最初创作的动机是什么?
上官晓梅:我最初创作的动机再简单不过了,或者说没有动机。第一次读张恨水的《啼笑因缘》,读完我就爱上了文学,我的文学之旅就这样开启。之后,才慢慢意识到,文学是为社会乃至历史服务的。
记者: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在虚构的世界,很多是现实的某种隐喻。在您的创作中,您是如何在写作中处理自我经验的呢?
上官晓梅:作者的自我经验如同深埋地下的种子,在某个角落,突然与现实发生碰撞,便由虚构来承载生根发芽。那些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人和事物,会被我拆解成细碎的元素,或者改变底色,融进故事脉络,我常说它们是铃铛,串在故事的主线上。这样可以赋予虚构的真实感,从而更接近生活的原本,让读者感受到似曾相识的人和事,产生更广泛的情感共鸣。
记者:许多作者会依靠经验写作,也会面临题材枯竭,想问问,您是如何过渡这个过程的?
上官晓梅:我不认为创作者会因经验面临题材枯竭。首先,经验不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恰恰相反,经验是能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酵,其次,不同年龄对事物有不同的理解和哲理,也就有了不同的经验。我认为,只要善于洞察和挖掘,经验是取之不尽的写作素材。
记者:市面上的小说,五花八门,写作的呈现方式也各不相同。您在创作之外,是否有阅读其他的小说。有哪些小说对您的创作有帮助,甚至影响到您的写作方式?
上官晓梅:在阅读方面,年轻的时候阅读比写作多,到了一定年龄写作比阅读多。阅读方面我追求读精。多读名作,比如《红楼梦》等等。对我创作有帮助的小说很多,无法一一列举。影响最深的是《红楼梦》。另外,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十月》《人民文学》《读者》等刊物,这些刊物有很多精品文章,我从中受益匪浅。
记者:这本《山潮》出版后,您还有什么新作值得期待?
上官晓梅:期待下一部长篇小说《先锋》出版,这是一个红色题材的小说,主人公是邵武第一个女共产党员,主人公和她的丈夫都是邵武革命先驱,同年牺牲,他们夫妻有很多值得挖掘的故事。
发布于:福建省广州配资公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