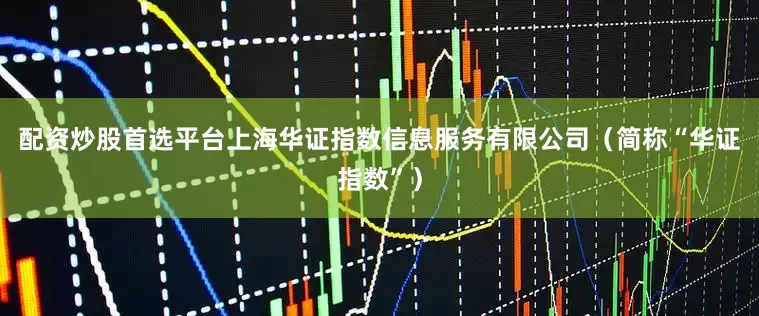5月19日夜晚,9岁围棋少年朱某鑫在比赛失利3天后坠楼身亡。
此前,他刚刚升上业余六段,在国内,同样年龄段内便冲到6段的棋童凤毛麟角。叠加“天才少年陨落”的叙事,这一新闻很快引起了众人关注。不少人将他的坠落,和其父对他可能存在的暴力行为关联起来。
事实真相如何,还需要更多的调查和还原。但这一事件让家暴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特别是部分中国家长习以为常的“棍棒底下出孝子”,究竟该算什么行为?
 朱某鑫手臂上的伤痕,图源网络。
朱某鑫手臂上的伤痕,图源网络。
事后再审视朱某鑫短短的一生,很难不让人同情和感叹:周围人的叙述中,其父对妻子似乎也有过暴力行为;在朋友圈里,其父也公开表示过要打朱某鑫,而在一些公开的照片里,也能看到孩子身上不知什么原因留下的伤痕。
 朱某鑫其父朋友圈,图源网络。
朱某鑫其父朋友圈,图源网络。
桩桩件件,尽管在法律层面上的家暴认定还需要更完整的证据链,但在朴素的道德观念里,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鸡娃”的范畴。
事实上,家庭领域的暴力,一直是一个长期存在、却也长期被遮蔽的问题。“棍棒底下出孝子”“虎爸虎妈”的观念一直有其受众,如知名钢琴家郎朗也曾经受其父的高压训练。但这一问题的隐秘性在于,“清官难断家务事”是人们长期以来的认知,即使看到孩子可能存在被家暴的可能性,也因为觉得父母管教小孩天经地义,而少有人帮助维权。
更不用说太多的家庭暴力发生在人后,本就不容易被看见。家庭单元因为有其私密性,反而变成了社会道德和公权力不好介入的场所。这说来也有几分荒唐:一个陌生人当街打小孩,可能会被围观群众很快制止,报警处理;但如果是家长打小孩,却可能因为是亲近之人所为,反而被遮蔽和掩盖了。
更实际的问题是,即使不考虑心理因素,未成年人的现实生存也和家长有着强关联。让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未成年人去反抗家庭暴力,这要求实在苛刻。更不用说,对于年纪更小的儿童来说,心智本身就没有发育成熟,很多时候和外界的沟通都依赖于家长的渠道,能不能接触到外界的帮助信息和机制,能不能明白自身有权利反抗暴力,都是个问题。
当家庭的私密性成为包庇暴力的借口时,破解家暴无法被及时制止的困境,首先就要破除“清官难断家务事”的陈旧观念。特别是当未成年人在家庭内部受到明显的暴力伤害时,很显然这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私域”范畴,必要时需要“公域”力量的介入。
在这一语境下,我们所讨论的,已不是哪位家长的子女受到的管教是否合理,而是公民的人身安全能否得到有效保障。在此基础上,社会应当形成的共识是:家庭从来不是法外之地。
当然,在“棍棒底下出孝子”等传统教育观念依然相当普遍的情况下,社会观念的转变可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无论如何,观念的不断革新和进步,会为法律和制度的完善提供土壤。
202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次修订时,就已体现了外部干预的信号。修订后的法律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发现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者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都有权劝阻、制止或者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控告。我国的反家暴法也明确规定,公安机关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应当及时出警,制止家庭暴力,按照有关规定调查取证,协助受害人就医、鉴定伤情。
这些法律条文的制定和更新,某种程度上具备观念上的引导意义,也意味着从传统单一的家庭亲权向国家亲权的加强。也就是说,当未成年的父母没有适当履行其义务时,国家可以介入其中,代替不称职的父母,以未成年人监护人的身份行使亲权,国家可以开始干预家务事了。
当然,观念的普及和更新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这一理念如何能在现实的案例中得到顺畅的落实。这必然不会是一个短时间内能解决的问题,但对青少年而言,这是国家与社会应然的许诺。
广州配资公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